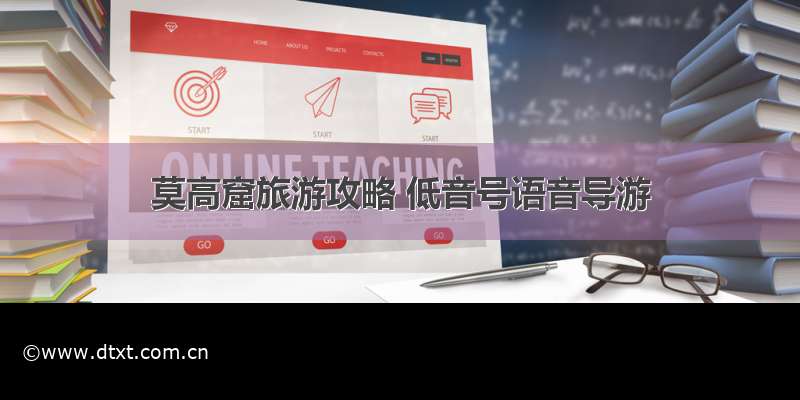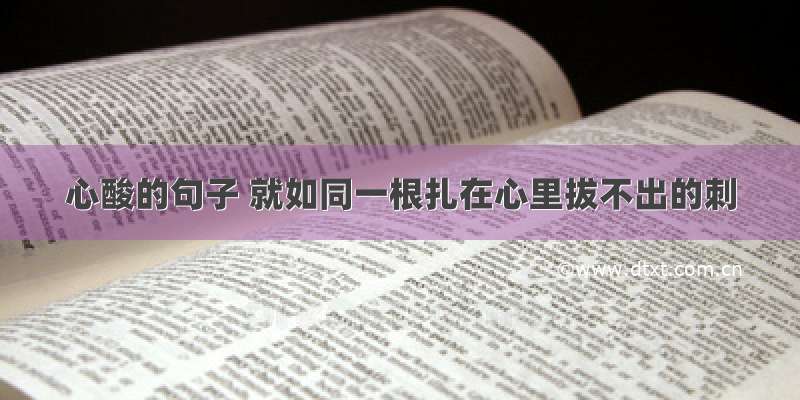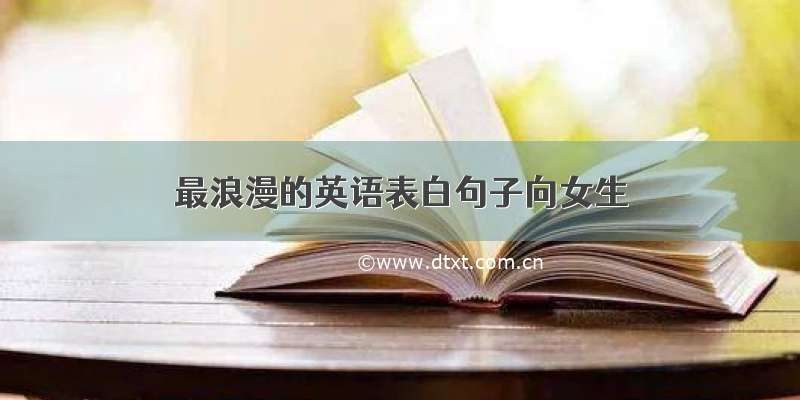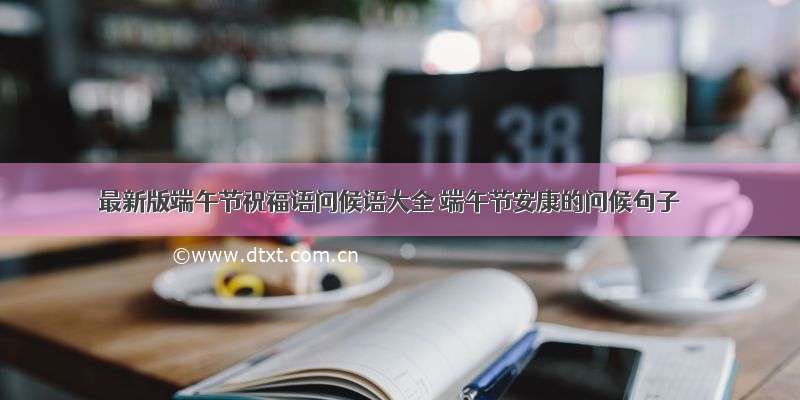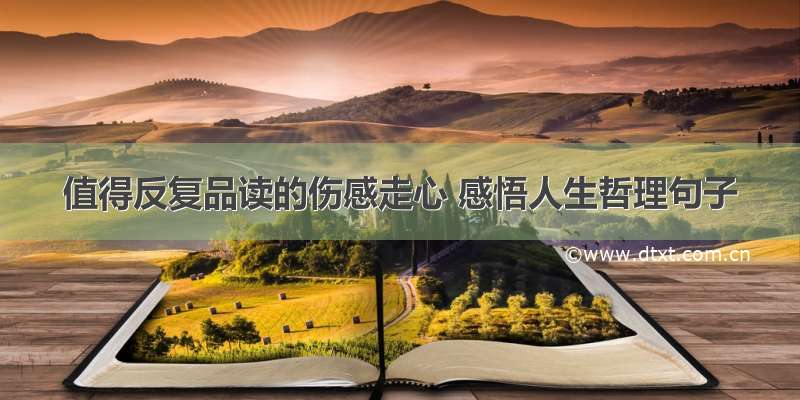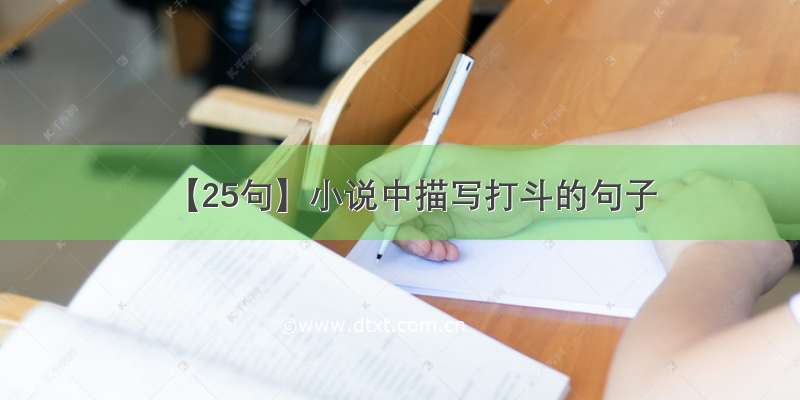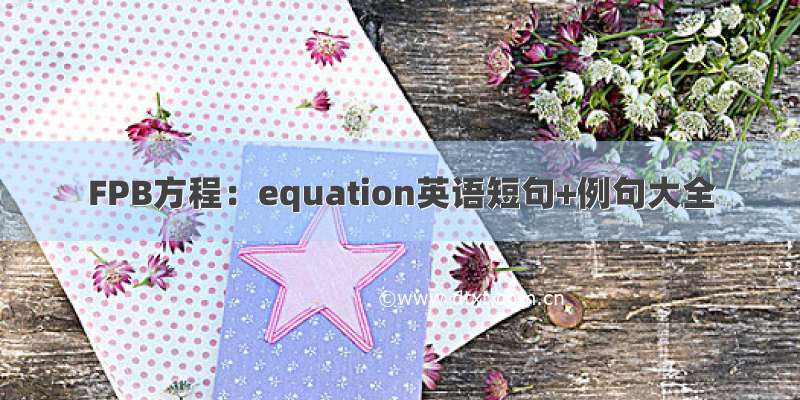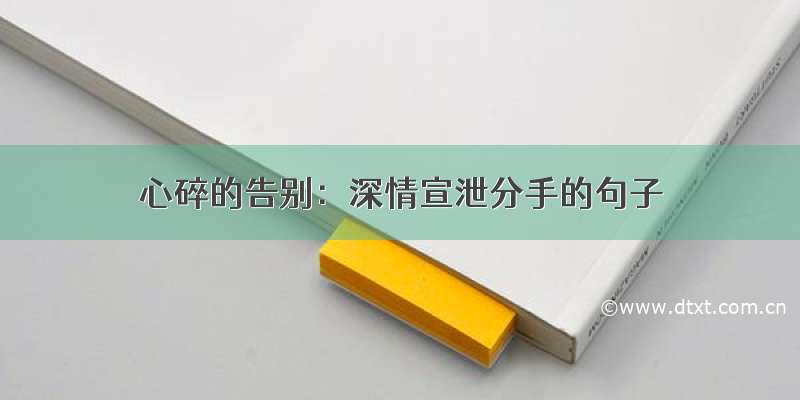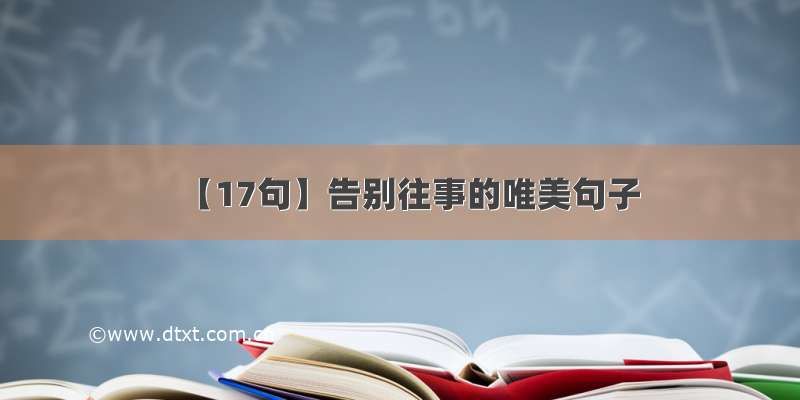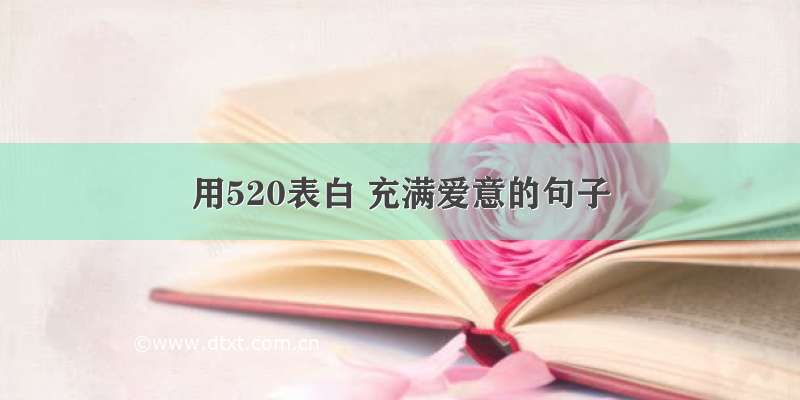「来源: |古籍 ID:weiguji」
一、伯希和对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察及收集
伯希和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这位年仅27岁的学者具有超人的语言禀赋,精通13种语言,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门生,能说流利的汉语。伯希和在敦煌的主要活动,是攫取了藏经洞的大量遗书和遗画,测绘了窟区地形和洞窟分布图,拍摄了洞窟内外景照片,编制了洞窟编号,撰写了洞窟笔记。1908年2月,伯希和考察队到达敦煌以后,对各民族的古文字包括西夏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伯希和在藏经洞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浏览挑选了文献精华。他的挑选原则是:非通行佛经,有年代供养人题记的佛经,社会文书,藏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希伯来文等民族和外来古文字。他对于西夏文的兴趣和了解,是与国际东方学界完全同步、并且几乎和柯兹洛夫在黑水城首次找到西夏文文献并寄呈给国际东方学会同时。
首先,伯希和敏感地调查了包括用西夏文刻画题写的题记:"我觉得,为了解释这些古籍的历史,惟有一名汉学家才可能做到并挑选出和利用最佳榜题和伴同它们的游人题记,它们全部或几乎全部是用汉文书写。我已经向您讲过西夏文(Si-hia)和八思巴文(Phag"s-pa)的游人题记,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数量不大。属于第一类(西夏文)的可能有20余方,属于第二类的勉强只有10方左右,它们全部都无法利用了。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以常用字书写的蒙古文和少许的婆罗谜文(brahmis)题记。"[1][P259]
其次,伯希和非常准确地依据有无西夏文文字来判断藏经洞封闭的年代。他在报告中说道:"第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便是该密室的大致年代的问题。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其汉文文书中的最后年号是宋代的最初几个年号:太平兴国(976年~983年)和至道(995年~997年)年间。此外,在整批藏经中,没有任何一个西夏字。因此,该龛是于11世纪上半叶封闭的,很可能是发生在1035年左右,在西夏人征服时代。人们乱无秩序地将汉文与藏文文书、绢画、帷幔、小铜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堆积在一起。人们可能会试图将成捆卷子散落开的混乱状态也归咎于对这次即将来临的入侵之恐惧,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这种文明在唐代时非常发达兴旺,后来一直艰难地勉强维持到五代时期。"由此可见,伯希和在藏经洞文献中搜索西夏文遍寻无计,才得出了藏经洞封闭于西夏占领敦煌以前的结论。这个强有力的论断至今仍是藏经洞断代的最主要依据,虽然关于其封闭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西夏的占领[2]。
在藏经洞中未能找到西夏文之后,伯希和在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开始在北区石窟继续寻求古代民族文字包括西夏文的资料。当他攫取了藏经洞"近全部写本的三分之一"之后,他宁可在北区石窟寻找和带回了我们所见到的支离破碎的西夏文残片,也不再眷恋藏经洞被留下的三分之二的哪怕是那么重要、完整、甚至璀璨光华的其他文献,可见西夏文文献哪怕是一些残片,对于国际学术界是多么的重要。
法国国家图书馆原登录西夏文藏品为217件,后继续查找出未编号的27件, 以及伯希和1938年在中国购买的经摺装《华严经》1件,木板写本1件,共著录了246件文献。对于西夏文材料,有百济康义编目的未刊稿,大致包括《华严经》、《二十一种行》、《瑜伽师地本母》、《正法念处经契》等等。国内学者一般都未见过,可能认为残片为多也不甚留意。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就忽略了文献学、书籍史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
二、法藏西夏文文献和俄国收藏的关系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是从莫高窟北区出土,和俄国、英国从黑水城挖掘的情况多有不同。就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来说,伯希和所获是最多的。由此来考察莫高窟遗存的西夏文献,法国藏品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主要的参照资料。
我们知道,1908年俄国柯兹洛夫考察队首先在黑水城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多数量、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西夏文献;然后,是英国斯坦因在同一地点得到了仅次于柯兹洛夫的重大收获。此后其他地点和时间中获得的西夏文献,都没有能够超出这两次考古发现。1917年宁夏灵武发现的元代西夏文献,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①,少量则为日本藏家收购;再以后在甘肃武威、宁夏银川等各地,也都各有发现。但是,无论如何,伯希和在北区石窟发现的西夏文残篇断简,是敦煌西夏文文献最多发现的一次。
西夏文文献资料的发现,一开始就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明确材料的背景,明了其间的联系,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我们从他的探险报告《西域考古记》已经大致了解。但是,我们似乎不知道他在北区石窟搜集到一些什么。
此后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北区石窟获取西夏文资料的情况:伯希和在洞窟笔记中说道:第181号洞,"该洞部分地被废物纸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们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古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在元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印经厂。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回鹘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1本几乎是完整的回鹘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从而使人联想到了我在第163号洞中于翻捆之外而发现的那个本子,我曾怀疑它是蒙古文而不是回鹘文的。如果它是蒙古文的,那么它就应该是自1900年以来才后放入第163号洞中的。这些书籍都已遭虫蛀和被撕毁了。"[3][P383] 第182号洞,"在于第181号洞发现一些写本残卷之后,我令人清理了第182号洞的过庭。大家在那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漂亮藏文写本残卷,它们是被故意撕碎的,有时已被部分地烧毁。其中仅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残书。"[3][P390] 这就是伯希和获取西夏文文献的地点和环境情况。
以后是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进行了发掘清理,涉及的范围包括南区和北区。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北区确实进行了发掘清理,甚至铲剥了遗留在今编D。B。77窟西壁的影塑背光。在哥萨克的照片中就有在北区洞窟清理积沙前的场景。推断奥登堡探险队所获部分材料源于北区石窟,和现在北区清理所获材料有联系[4],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俄罗斯藏馆却没有出自敦煌的西夏文特藏或者编号,而相反,一些出自黑水城的汉文文献却混在了敦煌汉文文献特藏中。由于俄国已经有科兹洛夫的黑水城特藏,由于科兹洛夫本人没有对黑水城的发掘进行严格的记录,由于俄藏黑水城藏品的海量和精彩,由于收藏过程中敦煌和黑水城文献的可能混淆,我们对于掺杂在敦煌特藏中的西夏时期的汉文文献,只能根据内容和经验来判断是获自敦煌还是获自黑水城②。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编号序列中,虽然有"Дx"即"敦煌"缩写的编号,但并非表示来自敦煌,而只是将错编到敦煌汉文文献序列的黑水城西夏文献重新甄别出来,而没有改变原先的编号。俄藏敦煌文献序列中为什么没有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文献呢?为什么就没有像伯希和获取的、敦煌研究院发掘采集的同类西夏文文献的残片呢?估计即使原先有西夏文文献,因为十分明显地表现为西夏文的文字特征,也很自然地会在整理、保管过程中被归入到黑水城西夏文特藏中。
已故敦煌学家孟列夫在《俄藏敦煌艺术品序言》中说:"在挖掘沙质地面时,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写卷和碎片、钱币、日常生活用品等。考察队中的人以他们发现的古代回鹘文木活字为特别重要。奥登堡院士编的考察队工作报告初稿未完稿上也有130件回鹘文木字的句子。这种活字和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有根本的区别,而奥登堡考察队发现的古物是活字印刷的最早的例证。可惜,我们不能知道这些木活字现在保存在什么地方。此类活字照片可见于著名的卡特T。F。Carter撰的《中国印刷发明史》,也可见于俄文《中华》论集KИTAЙ(1940年)中布那可夫Ю。B。БyHaKOBa的文章。"[5][P11] 而奥登堡的《千佛洞笔记》则详细记载了他们在伯希和发掘西夏文文献的P。181号窟即敦煌研究院编号D。464发掘的情形:"回鹘窟[D464][5][P325]:此窟填满了砖块、垃圾和砂土,为回鹘匠人由另一具有汉-吐蕃风格的窟改造而成,要准备确定其原先的布局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并要彻底清楚垃圾。我们只清理了主室,并找到许多手书的残块和130块回鹘活字的小木块。""清理回鹘窟[D。464]:1914年12月27日;为了割下此窟的一部分上有回鹘文字的水彩壁画,按照我们通常的惯例,首先要拍照。我和戈尔施科夫、戈莫诺夫去清理主室,那里堆满了砖块、窟顶上落下的小千佛残块、大量垃圾、动物骨骸以及来往过夜的人们留下的一些烟迹和烧焦的木柴。这里的垃圾看来多被人翻掘过,哪儿也没有层次,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发掘了,只不过就是把洞窟清理出来而已。但就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东西。除上述残迹外,还有一些很小的手书残片:有梵文的、库车文的、回鹘文的、吐蕃文的(一般的书法,还有斜体字,手书为蓝色带有金色字)、西夏文的(蓝地金字,残片),还有汉文的,此外还有回鹘文的、汉文的和西夏文的木刻残片。遗憾的是,这些残片实在太小,所以即使读通了也未必能说明什么。有价值的何止是西夏文和梵文的残片,这里的一切对于古文字学家都很重要。"
"此外,另一收获也十分有价值:105块刻有回鹘文字的木块。12月29 日我和戈尔施科夫又找到25块,现在一共有130块。""这些小块完全可以用作印刷活字,也可以印一些回鹘文木刻残片,这说明,那时人们已经不用木板,而是用活字印刷了。据我所知,这一事实至今尚无人提及。有的是符号、个别字母,有的是音节和单词、符号,还有一些是双面都有的。大多数是戈尔施科夫找到的,我和戈莫诺夫也找到了一部分。"
"12月30日,没有挖到底就结束了,只剩下砖块和沙子了……限于时间和精力,我便中止了这一无价值的发掘。水彩壁画我们决定不割了,只割了些小画像和拍照。"
《旅途照片》第216图考察队的说明文字是:"千佛洞。哥萨克契尔尼科夫在西藏洞窟里面(敦煌研究院蔡伟堂根据实地勘测校补说明为:北区洞窟B。464~465前室),不远处是大的西藏洞窟。1915年1月。"
以上是俄罗斯1914~1915年奥登堡考察队所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的发掘、采集情况。证明伯希和和奥登堡曾在北区石窟的同一地点进行了发掘。
三、敦煌研究院搜集的北区石窟的西夏文文献
从1988年开始,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领导了对莫高窟北区窟群的发掘整理,在伯希和、奥登堡发掘之后继续获得了一些西夏文文献。在考古报告中记载第464窟:"据有关资料揭示,1908年伯希和曾对此窟进行过挖掘,对此,他在《敦煌石窟笔记》中也作了记录。掘获的遗物有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回鹘文文献363件,西夏文文献200余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婆罗米文文献等。除此之外,1921年前后,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亦曾对第464 窟原西北侧室瘗埋的元代公主墓进行了盗掘,盗掘所获已不知下落。这两次盗掘给该窟的考古发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6][P53~54]"第464窟中室和后室,……个别地方有少量细沙层,厚0。03米,在此层内仅发现回鹘文木活字2枚。此层少量堆积应为伯希和劫余所留。……发现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梵文等文书残页、残片回鹘文木活字以及木构件花砖等。第464窟西北和东北侧室彼此相通, 故窟内堆积相同。……出土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文书残页、残片以及陶灯、陶印模、木匙等遗物。"其中包括有西夏文文书28件[6]。
综上所述,法国、俄国和敦煌研究院都先后在同一地点进行了发掘和搜集。首先是法国1908年,其次是俄国1914年,再后是敦煌研究院1988年开始历经数年对北区石窟的全面清理(1907年英国斯坦因似无记载)。这样的历史纪录,也向我们揭示了法、俄、敦煌研究院藏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同一地点的先后出土文物,其族群亲缘关系对于横向考察其相互联系、相互契合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我们已知其内容、形式所具备的共性的情况下,就尤其值得重视。--我们可以知道怎样去寻求缀合,怎样去利用所有的相关材料,怎样去相互证明,等等。
四、西夏文的发现、研究和刊布的简单历史
西夏王朝始于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建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即今宁夏银川市),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西夏共历10帝,享国190年。前期与北宋、辽鼎立,后期与南宋、金对峙,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了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
这是一个文化事业甚为发达的王朝。早在立国前夕,开国皇帝李元昊命令野利仁荣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民族文字,时称为"番字"、"番文"或"番书",后世称"西夏文"。自此在西夏全国同时通行西夏文和汉文、藏文。西夏王朝既注重党项族的传统文化,又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既提倡儒学,又弘扬佛教,用西夏文翻译了数以千卷计的大藏经,建立了众多的寺庙,创造了绚丽的艺术。但是,西夏王朝在正史中却只有简略的记载,在20世纪初西夏文物文献资料大量发现之前,西夏始终是一个充满神秘的王国,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西夏文是流行于宋初到元代的西北党项民族的文字,到清代已经完全死亡,无人能够释读。对于西夏文的重新认识,最早始于19世纪初,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发现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光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19世纪末,英、法学者考证北京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壁上六体文字是否有西夏文,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发掘到了西夏文写本,受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一种过去不甚了解、当时尚未解读的神秘文字。柯兹洛夫受命改变到别处探险的计划,在1909年再次到黑水城继续发掘寻找,在故城西面河岸边"著名的"大塔发现了一个皇家的"地下图书馆"。这次发现,被誉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并称的20世纪初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为西夏学和其他各项研究奠定了材料学的基础,并形成泱泱大观的崭新学科。
在科兹洛夫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曾从黑水城废墟中运出四十驼,骆驼运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有二万四千卷……那么就会明白那座著名的佛塔提供了多么巨大的财富。"③
后来中国学者罗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罗福成著《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进一步开展了专项研究。随后的是王静如《西夏研究》三辑④,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献,考证功力尤深,是当时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获得了法国茹莲奖。而陈寅恪先生《斯坦因Khara-Kt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7][P187,198],就是在王静如先生对英国所藏文献译证研究基础上,阐述了佛经译夏为汉的浩繁艰难、以汉证夏的勤苦精诚,西夏文献译自吐蕃、中原的不同来源,采用对译和意译的不同方法、以及西夏文流传直至明代万历之后的资料线索,等等。到8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夏学蓬勃兴起,出现了一批蜚声国际的优秀学者,如黄振华、史金波、李范文、陈炳应、龚煌城等等。在此之前,日本西夏学者也有很大的突破,如西田龙雄的《西夏语的研究》[8]、《西夏文华严经》等[9],也是西夏文研究的经典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纂的《俄藏黑水城文献》⑤,自1996年开始出版以来,逐步公布了全部俄藏汉文材料和部分西夏文世俗材料,对整个西夏学的推动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献》⑥。宁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以及宁夏大学等单位编纂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则完成了其他主要的藏品。而即将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则是在上述材料公布以后流失海外的最主要的西夏文藏品。自兹以往,已经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大多即已发表,西夏学的研究随着新材料的刊布,必将出现一个鼎新的局面。
法国、敦煌研究院的西夏文藏品是同宗同源的,法国藏品同俄国藏品也有部分的联系。法国藏品对于敦煌西夏文文献相互的证明、参考作用是其他馆藏无法替代的。所以法国藏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首要的意义是把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文献收集完整了,形成科学研究的完整的材料基础。
注释:
① 伯希和购买西夏文《华严经》Chinois10065。伯希和1938年购买西夏文《华严经》,其材料当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同一来源。
② 《俄藏敦煌文献》第五册彩色图版中集中刊登了混淆进入敦煌"Дx"序列的黑水城或者北宋的文献。又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 参见地理学会档案。转引自《俄藏黑水城文献》克恰诺夫《序言》,第12页。
④ 有关研究成果见王静如著:《西夏研究》第一辑至第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至十三。1933年,北平。
⑤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自1996年12月开始出版,至今已经出版汉文部分全部1~6册,西夏文世俗部分7~11册,并将继续完成西夏文世俗部分其他分册和西夏文佛教文献部分。
⑥ 《英藏黑水城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已经出版1~4卷。
【参考文献】
[1] 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耿升、唐健宾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2] 荣新江.藏经洞封闭原因[A]。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 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险记[M]。(耿升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 沙武田.俄藏敦煌艺术品与莫高窟北区洞窟关系蠡测[J]。敦煌学辑刊,2004,(2)。
[5]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艺术品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 西田龙雄.西夏语の研究Ⅰ,Ⅱ[M]。东京:座石室刊行会,1964~1966年.
[9]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Ⅲ[M]。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
附
聂鸿音:打开西夏文字之门,从黑水城头到涅瓦河畔
阿拉善黑水城遗址
没有资料表明早期的研究者是不是幻想过从哪里出土一本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字典。其实大家都知道,文物的出土大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与其没头苍蝇似的寻宝,不如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同时耐心地等待天赐的机缘。
给人们带来意外惊喜的是,机缘在毛利瑟的论文发表之后短短五年就出现了,而且竟然出现在距居庸关几近万里之遥的大漠当中。
让我们回溯到毛利瑟论文发表的20年前。
1882年的一天,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人和一个40岁出头的中年人在俄国斯摩棱斯克州的一所别墅里会面了。青年人叫科兹洛夫,是当地一所专科学校的学生,中年人是当时被誉为“中亚自然探险第一人”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生曾几次到中国考察,在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都留有足迹,他最杰出的考察成果是首次记述了黄河源、罗布泊和200多个新物种,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以他姓氏命名的“普氏野马”——equus ferus przewalskii。普尔热瓦尔斯基向科兹洛夫聊起了他传奇般的经历和今后几年的打算,年轻人显然是被充满挑战的未知世界深深吸引住了,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回忆道:“这一天决定了我整个一生的前程。”
圣彼得堡市“中亚自然探险第一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纪念碑
科兹洛夫从此便沿着他选定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次年就参加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率领的第四次中亚探险队。1887年,从圣彼得堡军事学校毕业的科兹洛夫已经成了一名军官,遥远的中国始终让他梦魂萦绕①。次年,被他视为导师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第五次探险途中病逝,科兹洛夫深深理解老师用生命去追寻的那个中国梦,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更加重大的探险活动来回报他的老师。
① 在当时的俄国只有军人才能承担探险任务。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军衔是少将。
年轻的科兹洛夫一直等了10年,独立探险的机会终于来了。
科兹洛夫
当时俄国的探险家都在被一座名叫哈拉浩特的古城折磨得神魂颠倒。传说中的这座古城位于蒙古的沙漠深处,有人在黄沙掩埋下的房屋里捡到过银器,当地人还盛传城内有一口很深的枯井,里面装满了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俄国人渴望找到这座古城,尤其渴望找到枯井里的宝藏,不过当地人并不愿意向外人透露古城的确切位置,所以探险者们一次次的希望总是变成失望,连科兹洛夫本人的首次尝试也是无功而返。多年以后科兹洛夫回忆道:“对哈拉浩特的想念完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和想象……我们是多么幻想着哈拉浩特和它那秘密的宝藏啊!”
科兹洛夫没有放弃。他经过充分的准备,协同著名探险家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制定了一个“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的行动计划,在1907年由皇家地理学会呈报给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在十多年前到过中国,自然向往中国的宝藏,于是他亲自召见了已经是陆军上校的科兹洛夫,并且在科兹洛夫一阵天花乱坠的赌咒发誓声中恩准了他的计划——命令外交部为探险队办理了赴中国的手续,特批3万卢布作为两年的经费②,另外还给了探险队十几支枪和足够的弹药。科兹洛夫激动得难以自制,他下决心找到最珍贵、最丰富的藏品来报效沙皇。他告别沙皇的一句话是:“请您为我们祝福吧!”可是尼古拉二世没有回应,因为他心里明白,当时罗曼诺夫王朝的帝俄政治已经是风雨飘摇。
② 3万卢布在20世纪初是一笔巨款,尽管在90年代初已经贬值得只能买20个面包。
科兹洛夫和他的探险队
1908年3月,科兹洛夫率领他的探险队从乌兰巴托出发,在蒙古人的指引下来到了土尔扈特王爷的驻地,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境内,那附近最著名的古代遗址是居延古城,最著名的自然景观是一望无际的居延海和深秋金色的胡杨林③。
③ 那时王爷府的具体位置还不清楚,现在能见到的额济纳王爷府是1940年在达来库布镇近郊新建的,前院有1998年树立的“纪念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三百周年”汉白玉纪念碑。
土尔扈特王爷达西贝勒的祖先大约在17世纪初从新疆迁徙到了俄罗斯伏尔加河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一带,重新建立了一个“土尔扈特汗国”,也就是俄罗斯史书上说的“卡尔梅克汗国”。由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当地治理不当,民众与政府间的武装冲突频发,最终迫使土尔扈特人在1771年决定举族回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17万人的东归队伍历时三年,冲破了哥萨克骑兵的重重截击,在付出了近一半人的生命代价之后,终于从新疆伊犁进入了祖国境内。东归英雄们的壮举让乾隆皇帝深深体会到了自己的伟大,他随即下令把土尔扈特人安置在祖国西北水草丰饶的地区,同时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了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并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命人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成两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外八庙”之一的普陀宗乘之庙内永久保存。
反映土尔扈特部东归的画作
东归英雄的子孙不失蒙古人传统的豪放性格。达西贝勒在胡杨林边接待了探险队,并不计较探险队的成员里有当年哥萨克骑兵的后人。科兹洛夫对达西贝勒表示了充分的尊重,酒过三巡之后送上了礼物——几支步枪,达西贝勒马上表示愿意全力协助探险队去往那个神秘的地方。
几天以后,探险队五名成员在土尔扈特向导的带领下进入了巴丹吉林沙漠,走了30多公里后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古城。这座面积不及天安门广场一半的长方形小城坐落在额济纳河干涸的古河道边,夯土城墙大约有10米高,保存得还算不错,瓮城、马面之类防御建筑一应俱全,西北角的佛塔是这座城最显著的标志。城的名字“哈拉浩特”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黑城”,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习惯叫它“黑水城”,是意译了党项语的“额济纳”。这座城始建于西夏,是河西走廊通向漠北的要冲,也是西夏“黑水镇燕军司”的驻所。城市1226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占领,后来成了元代的亦集乃路总管府所在地。城区在元代经过扩建,大约在14世纪下半叶因额济纳河流改道、水源断绝、绿洲沙化而遭废弃。
黑水城远眺(2010年)
20世纪初的黑水城内满是瓷器和瓦器的碎片,完整的物件只有谁也搬不走的石磨盘。所有的房屋都已坍塌,据残存的土坯墙和地基还可以勉强分辨出当年的居舍和街道格局。有一处稍大些的院落好像是官府,可是当年官员们贮存的财物早已不知去向。探险队雇佣了些民工,每天除了运送生活必需品以外,就几乎是拿着铁锹和镐头在城内漫无目标地挖掘。一群人灰头土脸地折腾了将近半个月,还打开了两座小塔,传说中的枯井宝藏自然没有踪影,只得到了一些残破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不知用什么文字写成的字纸、账簿和几本佛经。不过科兹洛夫本人对这些收获也还勉强表示满意,他把所有的东西装了十个箱子,并附上一份简单的发掘报告,通过蒙古邮局寄往圣彼得堡,希望地理学会对上面的文字做出鉴定,而他自己则率队离开了黑水城,前往四川和青海交界地区继续他的探险计划。
黑水城内被流沙掩埋的房屋(2010年)
通过对照卜士礼和戴维理亚的研究,俄国地理学会马上判定科兹洛夫寄来的文字样品正是和居庸关文字一样的西夏文。学会的副会长格里高利耶夫在当年年底给科兹洛夫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他在黑水城发现的东西是举世罕见的西夏遗存,同时要求他放弃四川的探险计划,直接转回那座古城,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全面发掘,以求获取更多的贵重文物。于是,科兹洛夫率队于1909年5月底再次来到了黑水城,热情爽快的达西贝勒也帮他们雇好了民工,向工地运送粮食、水和羊肉。
其实要对古城进行全面发掘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城内大约五分之一的面积已经被流沙覆盖,有些地方的沙山甚至高过了城墙。即使请愚公带着全家来移山,至少也要让他的小孙子干到他那个岁数④。
④ 1983年和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黑水城内进行了号称是“最全面彻底”的发掘,但这些被流沙掩埋的面积还是不得不被算在“全面彻底”之外了。
按照考古的常识,最有可能获取珍贵文物的地方是坟墓,特别是王公贵族的坟墓,可是科兹洛夫让人在城外找了几天,竟然没有发现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墓葬群——难道黑水城的居民个个都是长生不死么?要不就是在火葬之后被扬了灰了⑤?无奈之下,探险队只好一天天地在37度高温下重复着一年前那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在相对裸露的地面上收集着碎瓷器和烂字纸,偶尔找到一尊小佛像或者一本撕得没剩几页的小书都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兴奋。科兹洛夫特别希望找到一双鞋,可是终未如愿⑥。
⑤ 距黑水城几十公里外有极大一片散落的民居遗址,当地人叫做“绿城”,那里却是有坟墓的,至今还有人不断在那里盗掘,但好像没听说发现过什么有价值的随葬品。
⑥ 200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戴忠沛来到了黑水城,他在城内一堵坍塌不久的土坯墙里拨弄了十几分钟,忽然拎出个东西大声叫了起来:“看哪,我发现了西夏的破鞋!”
当初的期望和现实所获的巨大反差让科兹洛夫的心情糟透了,他不久就对城内彻底丧失了信心,近乎绝望的目光转向西城墙外400米的一座十几米高的佛塔——气急败坏地命令民工们:“挖开它!”
科兹洛夫探险队在挖掘古塔
谁也没有想到,这句毫无文物保护意识的混账话竟然为整个国际东方学界带来了无比巨大的财富,也保送他这个从未打过仗的上校没过多久就当上了将军。中国人在多年后想起这句话时的心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20世纪末,几个中国的西夏学家在瓦西里岛上斯摩棱斯克公墓的树丛中找到了科兹洛夫的长眠之所,思来想去,他们最终还是点燃了一支中华牌香烟,权当香烛供奉在这位“文物盗窃分子”的墓前。
1909年6月12日,科兹洛夫坐在帐篷里烦闷得要发疯,这时突然有人过来报知,刚挖开的那座塔里存放着数不清的书籍和彩塑的佛像。科兹洛夫一阵狂喜,跑到现场一看——那竟然是真的!黑水城送给了他一个完整的书库!
我们不知道那时的科兹洛夫怎样估算他这个书库的价值,那真的能跟传说中的枯井宝藏相比么?不过无论如何,梦里的金银毕竟不如现实的烂纸,科兹洛夫应该满足了。
科兹洛夫后来声称他的黑水城考古工作全都是以规范程序进行的,但俄国学者都知道那是吹牛。事实上佛塔的清理工作一共进行了9天,绝大多数时间科兹洛夫都不在现场指挥,只是在帐篷里坐等民工们把沾满灰土的书籍乱七八糟地搬运过来。没有发掘记录,没有现场照片,甚至没有写下完整的日记,所以后来的研究者无从知道塔室的形制,更无从知道塔内文物的摆放次序。而科兹洛夫本人则因为不懂得汉文和西夏文,所以只能依据开本的大小对书籍作了混乱的分装,并不知道700年后重生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和与居庸关咒语内容相当的西夏文抄本也在其中。
后来人们根据科兹洛夫的零散回忆猜测,那座塔的内部分为两层,下层好像被布置成了一间修行室,周边的墙上挂着西藏风格的佛画,墙边摆放的彩色泥塑佛教造像围成一圈,一律面向塔室中央,上千册书籍就整齐地叠放在塔室中部,好像要供修行者随时取出阅读,只是压在最下层的书籍已经发霉。与此相对的是,塔室上层的书却堆放得极其凌乱,似乎是在很久以后被什么人成批地扔进去的。也许《掌中珠》就是被扔进塔室上层的,否则后来运到圣彼得堡时就不应该那么零散。塔室的北墙边有一具人骨架,显出临终时打坐的姿势。科兹洛夫猜测那是当地的活佛,于是把他的头部砍下来带回了圣彼得堡,可是后来对头骨的人种学鉴定却表明那属于一个50来岁的女性。据俄罗斯方面说,那个头骨和不同来历的其他头骨一起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的民族学研究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搬来搬去弄乱了藏品标签,所以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哪个了。
跟随探险队的骆驼只有40匹,科兹洛夫没办法带走这次出土的全部文物,只好把书籍、字纸和佛画全部装箱,而把一部分佛教彩塑留了下来。这批彩塑被摆在一起拍了个“全家福”,然后就埋在了黑水城的南墙外。科兹洛夫在1926年底再次来到黑水城时可能又拿走了几件,因为我们看到照片里的个别塑像后来摆放在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而大多数塑像则至今不知所终。多年以后,我国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都曾动过寻找这批塑像的念头,但是具体工作没能实施。
古塔内的佛教彩塑
科兹洛夫探险队从蒙古运回圣彼得堡的文物临时收藏在皇家地理学会顶层的一间空房子里,第二年就被分到涅瓦河畔两处相邻的地方:泥塑、唐卡等艺术品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书籍和字纸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的亚洲博物馆。亚洲博物馆曾经几易其名,1956年改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90年代起改称圣彼得堡分所,前任所长是国际西夏学泰斗、中国西夏学界的老朋友克恰诺夫。研究所在2007年改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现任所长是唐史专家和敦煌学家波波娃。这个研究所多年来一直被看做西夏学和敦煌学的圣地。
克恰诺夫和波波娃在黑水城(2010年)
据推测,黑水城文献的总量应该不亚于敦煌藏经洞,其中西夏文文献经初步整理后的编号至今已经超过9000,但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所以没人能准确说出科兹洛夫拿回的文献到底有多少,据科兹洛夫自己估计有24000卷,但这个数字始终没办法核实。好在里面的字典早已被伊凤阁大致拣选出来整理完毕,尽管除《掌中珠》以外的字典都是纯用西夏文编成的,但人们可以凭借《掌中珠》里用汉文给出的西夏字义和字音基本读懂那些字典,一步步地扩大自己掌握的词汇量,从而把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应用到其他的西夏文献解读中去。
西夏建国的早期亟须普及新创制的本民族文字,中晚期又建立了自己的科举制度,这使得西夏朝野都不约而同地对编纂字典和童蒙识字课本倾注了热情。在汉文化的强大影响下,几乎每种类型的中原字典或者童蒙识字课本都可以在西夏找到自己的影子。例如中原有《广韵》和《说文解字》,西夏就有《文海》;中原有《礼部韵略》,西夏就有《文海宝韵》;中原有《韵镜》,西夏就有《五音切韵》;中原有《尔雅》,西夏就有《同义》;中原有《千字文》,西夏就有《置掌碎金》;中原有《纂要》,西夏就有《要集》。不过西夏人也并非只会模仿邻居,有两种字书显示了他们在中原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一种是《同音》,编者富于创造性地把《广韵》按韵母列字的编排方法改为按声母列字,另一种当然就是在20世纪使用率最高的《番汉合时掌中珠》。
选自“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打开西夏文字之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