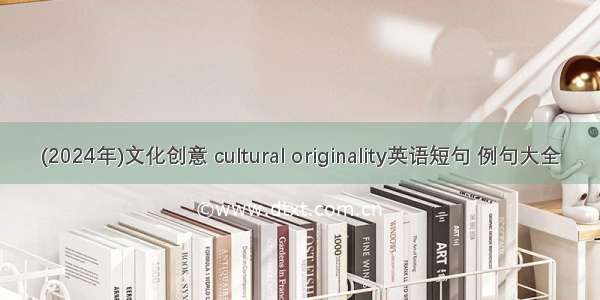语言的形式之所以能是美的,因为它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这些美都是音乐所具备的,所以语言的形式美也可以说是语言的音乐美。在音乐理论中,有所谓音乐的语言;在语言形式美的理论中,也应该有所谓语言的音乐。音乐和语言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音乐和语言都是靠声音来表现的,声音和谐了就美,不和谐就不美。整齐、抑扬、回环,都是为了达到和谐的美。在这一点上,语言和音乐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语言形式的美不限于诗的语言,散文里同样可以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从前有人说,诗是从声律最优美的散文中洗练出来的;也有人意识到,具有语言形式美的散文却又正是从诗脱胎出来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是语言,就可能有语言形式美存在,而诗不过是语言形式美的集中表现罢了。
[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局部)
01
整齐的美
在音乐上,两个乐句构成一个乐段。最整齐匀称的乐段是由长短相等的两个乐句配合而成的,当乐段成为平行结构的时候,两个乐句的旋律基本上相同,只是以不同的终止来结束,这样就形成了整齐的美。同样的道理应用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语言的对偶和排比。对偶是平行的、长短相等的两句话,排比则是平行的、但是长短不相等的两句话,或者是两句以上的、平行的、长短相等的或不相等的话。
远在第二世纪,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就以善用排比的语句为人们所称道。直到现在,语言的排比仍然被认为修辞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排比作为修辞手段虽然是人类所共有的,对偶作为修辞手段却是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当然,和汉语同一类型的语言也能有同样的修辞手段。)。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虽然双音词颇多,但是这些双音词大多数都是以古代单音词作为词素的,各个词素仍旧有它的独立性。这样就很适宜于构成音节数量相等的对偶。对偶在文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骈体文和诗歌中的偶句。
骈偶的来源很古。《易·乾·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诗·召南·草虫》说:“喓喓草虫,趯趯阜螽。”《邶风·柏舟》说:“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小雅·采薇》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例子可以举得很多。
六朝的骈体文并不是突然产生的,也不是由谁规定的,而是历代文人的艺术经验的积累。秦汉以后,文章逐渐向骈俪的方向发展。例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说:“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又说:“节同时异,物是人非。”这是正向着骈体文过渡的一个证据。从骈散兼行到全部骈俪,就变成了正式的骈体文。
对偶既然是艺术经验的积累,为什么骈体文又受韩愈等人排斥呢?骈体文自从变成一种文体以后,就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缺乏灵活性,从而损害了语言的自然。骈体文的致命伤,还在于缺乏内容,言之无物。作者只知道堆砌陈词滥调,立论时既没有精辟的见解,抒情时也没有真实的感情。韩愈所反对的也只是这些,而不是对偶和排比。他在《答李翊书》里说:“惟陈言之务去。”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他并没有反对语言中的整齐的美。没有人比他更善于用排比了:他能从错综中求整齐,从变化中求匀称。他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又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样错综变化,就能使文气更畅。尽管是这样,他也还不肯放弃对偶这一个重要的修辞手段。他的对偶之美,比之庾信、徐陵,简直是有过之无不及。试看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所写的“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在《进学解》所写的“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在《答李翊书》所写的“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哪一处不是文质彬彬、情采兼备的呢?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整齐而不雷同,匀称而不呆板,语言中的对偶和排比,的确可以构成形式的美。在对偶这个修辞手段上,汉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这一艺术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的。
02
抑扬的美
在音乐中,节奏是强音和弱音的周期性的交替,而拍子则是衡量节奏的手段。譬如你跳狐步舞,那是四拍子,第一拍是强拍,第三拍是次强拍,第二、四两拍都是弱拍;又譬如你跳华尔兹舞,那是三拍子,第一拍是强拍,第二、三两拍都是弱拍。
节奏不但音乐里有,语言里也有。对于可以衡量的语音单位,我们也可以有意识地让它们在一定时隙中成为有规律的重复,这样就构成了语言中的节奏。诗人常常运用语言中的节奏来造成诗中的抑扬的美。西洋的诗论家常常拿诗的节奏和音乐的节奏相比,来说明诗的音乐性。在这一点上说,诗和音乐简直是孪生兄弟了。
由于语言具有民族特点,诗的节奏也具有民族特点。音乐的节奏只是强弱的交替,而语言的节奏却不一定是强弱的交替;除了强弱的交替之外,还可以有长短的交替和高低的交替(上文所说的都是可衡量的语音单位,因音的长度、强度、高度都是可以衡量的。)。譬如说,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长短音的区别很重要,希腊诗和拉丁诗的节奏就用的是长短律;在英语和俄语中,轻重音的区别很重要,英国诗和俄国诗的节奏就用的是轻重律。因此,希腊、罗马诗人的抑扬概念,跟英、俄诗人的抑扬概念不同。尽管用的是同样的名称,希腊、罗马诗人所谓抑扬格指的是一短一长,英、俄诗人指的是一轻一重;希腊、罗马诗人所谓扬抑格指的是一长一短,英、俄诗人指的是一重一轻;希腊、罗马诗人所谓抑抑扬格指的是两短一长,英、俄诗人指的是两轻一重;希腊、罗马诗人所谓扬抑抑格指的是一长两短,英、俄诗人指的是一重两轻。
汉语和西洋语言更不相同了。西洋语言的复音词很多,每一个复音词都是长短音相间或者是轻重音相间的,便于构成长短律或轻重律;汉语的特点不容许有跟西洋语言一样的节奏。那么,汉语的诗是否也有节奏呢?
从传统的汉语诗律学上说,平仄的格式就是汉语诗的节奏。这种节奏,不但应用在诗上,而且还应用在后期的骈体文上,甚至某些散文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灵活地用上了它。
平仄格式到底是高低律呢,还是长短律呢?我倾向于承认它是一种长短律。汉语的声调和语音的高低、长短都有关系,而古人把四声分为平仄两类,区别平仄的标准似乎是长短,而不是高低。但也可能既是长短的关系,又是高低的关系。由于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占优势,汉语诗的长短律不可能跟希腊诗、拉丁诗一样,它有它自己的形式。这是中国诗人们长期摸索出来的一条宝贵的经验。
汉语诗的节奏的基本形式是平平仄仄,仄仄平平。这是四言诗的两句。上句是两扬两抑格,下句是两抑两扬格。平声长,所以是扬;仄声短,所以是抑。上下两句抑扬相反,才能曲尽变化之妙。《诗·周南·关雎》诗中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就是合乎这种节奏的。每两个字构成一个单位,而以下字为重点,所以第一字和第三字的平仄可以不拘。《诗·卫风·伯兮》诗中的“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样是合乎这种节奏的。在《诗经》时代,诗人用这种节奏,可以说是偶合的、不自觉的,但是后来就渐渐变为自觉的了。曹操《短歌行》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土不同》的“心常叹怨,戚戚多悲”;《龟虽寿》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些就不能说是偶合的了。这两个平仄格式的次序可以颠倒过来,而抑扬的美还是一样的。曹操的《土不同》的“水竭不流,冰坚可蹈”;《龟虽寿》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是这种情况。
《曹操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有了平仄的节奏,这就是格律诗的萌芽,这种句子可以称为律句。五言律句是四言律句的扩展;七言律句是五言律句的扩展。由此类推,六字句、八字句、九字句、十一字句,没有不是以四字句的节奏为基础的。
五字句比四字句多一个字,也就是多一个音节。这一个音节可以加在原来四字句的后面,叫做加尾;也可以插入原来四字句的中间,叫做插腰。加尾要和前一个字的平仄相反,所以平平仄仄加尾成为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加尾成为仄仄平平仄;插腰要和前一个字的平仄相同,所以平平仄仄插腰成为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插腰成为仄仄仄平平。
五言律诗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逐渐形成的过程。曹植的《箜篌引》有“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白马篇》有“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赠白马王彪》有“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情诗》有“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这些已经是很完美的五言律句了,但是这种上下平仄相反的格式还没有定型化,曹植还写了一些平仄相同(后人叫做失对)的句子,例如《美女篇》的“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又说:“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到了这个时候,诗的平仄逐渐有了定格。但是齐梁的诗仍有不对、不粘的律句。沈约自己的诗《直学省秋卧》:“秋风吹广陌,萧瑟入南闱。愁人掩轩卧,高窗时动扉。虚馆清阴满,神宇暖微微。网虫垂户织,夕鸟傍檐飞。缨佩空为忝,江海事多违。山中有桂树,岁暮可言归。”分开来看,句句都是律句;合起来看,却未能做到多样化的妙处,因为不粘、不对的地方还很多。到了盛唐,律诗的整个格式才算定型化了。
从五言律诗到七言律诗,问题很简单:只消在每句前面加上平仄相反的两个字就成了。从此以后,由唐诗到宋词,由宋词到元曲,万变不离其宗,总不外是平仄交替这个调调儿(关于诗词的格律,参看拙著《诗词格律》和《诗词格律十讲》,这里不再叙述。)。七减四成为三字句,二加四成为六字句,三加五成为八字句,四加五或二加七成为九字句,如此等等,可以变出许多花样来。甚至语言发展了,声调的种类起了变化,而平仄格式仍旧不变。试看马致远的《秋思》:“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这个曲调是《拨不断》,头两句都要求收音于平声,第五句要求收音于仄声,按《中原音韵》,“竭”和“绝”在当时正是读平声,“缺”字在当时正是读仄声(去声)。当时的入声字已经归到平、上、去三声去了,但是按照当代的读音仍旧可以谱曲。
《诗词格律》
直到今天,不少的民歌,不少的地方戏曲,仍旧保存着这一个具有民族特点的、具有抑扬的美的诗歌节奏。汉语的声调是客观存在的,利用声调的平衡交替来造成语言中的抑扬的美,这也是很自然的。
……
新诗的节奏不是和旧体诗词的节奏完全绝缘的,特别是骈体文和词曲的节奏,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很多。已经有些诗人在新诗中成功地运用了平仄的节奏。现在试举出贺敬之同志《桂林山水歌》开端的四个诗行来看: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这四个诗行同时具备了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整齐的美很容易看出来,不必讨论了。回环的美下文还要讲到,现在单讲抑扬的美。除了衬字(“的”字)不算,“神姿仙态桂林山”和“如情似梦漓江水”,十足地是两个七言律句。我们并不说每一首新诗都要这样做,但是当一位诗人在不妨碍意境的情况下,能够锦上添花地照顾到语言形式美,总是值得颂扬的。
不但诗赋骈体文能有抑扬的美,散文也能有抑扬的美,不过作家们在散文中把平仄的交替运用得稍为灵活一些罢了。我从前曾经分析过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认为其中的腔调抑扬顿挫,极尽声音之美。例如“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这两句话的平仄交替是那样均衡,决不是偶合的。前辈诵读古文,摇头摆脑,一唱三叹,逐渐领略到文章抑扬顿挫的妙处,自己写起文章来不知不觉地也就学会了古文的腔调。我们今天自然应该多作一些科学分析,但是如果能够背诵一些现代典范白话文,涵泳其中,抑扬顿挫的笔调,也会是不召自来的。
03
回环的美
回环,大致说来就是重复或再现。在音乐上,再现是很重要的作曲手段。再现可以是重复,也可以是模进。重复是把一个音群原封不动地重复一次,模进则是把一个音群移高或移低若干度然后再现。不管是重复或者是模进,所得的效果都是回环的美。
诗歌中的韵,和音乐中的再现颇有几分相像。同一个音(一般是元音,或者是元音后面再带辅音)在同一个位置上(一般是句尾)的重复,叫做韵。韵在诗歌中的效果,也是一种回环的美。当我们听人家演奏舒伯特或托赛利的小夜曲的时候,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个音群,我们不但不觉得讨厌,反而觉得很有韵味;当我们听人家朗诵一首有韵的诗的时候,每句或每行的末尾总是同样的元音(有时是每隔一句或一行),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反而觉得非常和谐。
依西洋的传统说法,韵脚是和节奏有密切关系的。有人说,韵脚的功用在于显示诗行所造成的节奏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参看A·Dorchain《诗的艺术》第102页。)。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看法是以西洋诗为根据的,对汉语诗来说不尽适合。因为汉语诗不都是有节奏的,也不一定每行、每句都押韵。但是,从诗的音乐性来看韵脚,这一个大原则是和我们的见解没有矛盾的。
散文能不能有韵?有人把诗歌称为韵文,与散文相对立,这样,散文似乎就一定不能有韵语了。实际上并不如此。在西洋,已经有人注意到鲁索在他的《新爱洛伊丝》里运用了韵语(参看A·Dorchain《诗的艺术》27页。)。在中国,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易经》和《老子》大部分是韵语,《庄子》等书也有一些韵语。古医书《黄帝内经》(《素问》《灵枢》)充满了韵语。在先秦时代,韵语大约是为了便于记忆,而不是为了艺术的目的。到了汉代以后,那就显然是为了艺术的目的了。如果骈体文中间夹杂着散文叫做“骈散兼行”的话,散文中间夹杂着韵语也可以叫做“散韵兼行”。读者如果只看不诵,就很容易忽略过去;如果多朗诵几遍,韵味就出来了。
例如枚乘《上书谏吴王》一开头“臣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汉书》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今依李兆洛《骈体文钞》。),就是韵语。下文:“系绝于天,不可复结;队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结”“出”“发”“脱”四字押韵,“天”“山”“安”“难”四字押韵。又:“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闻”“言”押韵,“知”“为”押韵。又:“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自来?”“基”“胎”“来”押韵。又:“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差”“过”押韵。又:“夫十围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也。”“蘖”“绝”“拔”押韵,“生”“形”押韵。
又如柳宗元《愚溪诗序》:“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这里是“违”和“归”押韵,“夷”和“知”押韵(也可以认为四字一起押韵,算是支、微通押)。
又如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浏如。既焚既酿,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值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徐。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这里是“芜”和“涂”押韵,“丘”和“浏”押韵(虚字前韵),“出”和“位”押韵(出,尺类切,读chuì),“舒”“徐”和“隅”押韵,“仆”和“怒”押韵。
又如大家所熟悉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鱼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里“霏”和“开”押韵(不完全韵),“空”和“形”押韵(不完全韵),“摧”和“啼”押韵(不完全韵),“讥”和“悲”押韵,“明”“惊”和“顷”“泳”“青”押韵(平仄通押),“璧”和“极”押韵,“忘”和“洋”押韵。作者并不声明要押韵,他的押韵在有意无意之间,不受任何格律的约束,所以可以用不完全韵,可以平仄通押,可以不遵守韵书的规定(如“讥”和“悲”押,“明”“惊”和“青”押,“璧”和“极”押)。这一条艺术经验似乎是很少有人注意的。
赋才是真正的韵文。我们主张把汉语的文学体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散文,第二类是韵文,第三类是诗歌。韵文指的就是赋,有人把赋归入散文,那是错误的(陈钟凡先生的《中国韵文通论》把诗、赋都归韵文,那比把赋归入散文好得多。)。单从全部押韵这一点说,它应该属于诗的一类。但是有许多赋并没有诗的意境,所以只好自成一类,它是名副其实的韵文。赋在最初的时候,还不十分注意对偶,更无所谓节奏。到了南北朝,赋受骈体文的影响,不但有了对偶,而且逐渐有了节奏。例如庾信的《哀江南赋》,等于后期的骈体文加韵脚,兼具了整齐的美、节奏的美、回环的美,这简直就是一篇史诗。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则又别开生面,多用“也”“矣”“焉”“哉”“乎”,少用对偶和节奏,使它略带散文气息,而韵脚放在“也”“矣”“焉”“哉”“乎”的前面,令人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遥远地继承了《诗经》的优点,而又加以发展的一种长篇抒情诗。我常常设想:我们是否也可以拿“呢”“吗”“的”“了”来代替“也”“矣”“焉”“哉”“乎”来尝试一种新的赋体呢?成功的希望不是没有的。
[金]武元直 《赤壁图》(局部)
韵脚的疏密和是否转韵,也有许多讲究。《诗经》的韵脚是很密的:常常是句句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即以句句用韵来说,韵的距离也不过像西洋的八音诗。五言诗隔句用韵,等于西洋的十音诗。早期的七言诗事实上比五言诗的诗行更短,因为它句句押韵(所谓柏梁体),事实上只等于西洋的七音诗。从鲍照起,才有了隔句用韵的七言诗,韵的距离就比较远了。我想这和配不配音乐颇有关系。词的小令最初也配音乐,所以韵也很密。曲韵原则上也是很密的,只有衬字太多的时候,韵才显得疏些。直到今天的京剧和地方戏,还保持着密韵的传统,就是句句用韵。在传唱较久的京剧或某些地方戏曲中,还注意到单句押仄韵,双句押平韵(如京剧《四郎探母》和《捉放曹》等),这大约也和配音乐有关。
一韵到底是最占势力的传统韵律。两句一换韵比较少见,必须四句以上换韵才够韵味,而一韵到底则最合人民群众的胃口。打开郑振铎的一部《中国俗文学史》来看,可以说其中的诗歌全部是一韵到底的。我们知道,元曲规定每折必须只用一个韵部。例如关汉卿《窦娥寃》第一折押尤侯韵,第二折押齐微韵,第三折押先天韵,第四折押皆来韵。直到现代的京剧和地方戏,一般也都是一韵到底的。例如京剧《四郎探母·坐宫》押言前辙,《捉放曹·宿店》押发花辙。在西洋,一韵到底的诗是相当少的。可见一韵到底,也表现了汉语诗歌的民族风格。
双声、叠韵,也是一种回环的美。这种形式美在对仗中才能显示出来。有时候是双声对双声,如白居易《自河南经乱……》“田园零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以“零落”对“流离”;又如李商隐《落花》“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以“参差”对“迢递”。有时候是叠韵对叠韵,如杜甫《秋日荆南述怀》“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以“苍茫”对“展转”;又如李商隐《春雨》“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以“晼晚”对“依稀”。又有以双声对叠韵的,如杜甫《咏怀古迹》第一首“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以“支离”对“漂泊”(漂:滂母字;泊:并母字,这是旁纽双声。);又如李商隐《过陈琳墓》“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以“埋没”对“荒凉”。双声、叠韵的运用并不限于联绵字,非联绵字也可以同样地构成对仗。
杜甫是最精于此道的。现在随手举出一些例子,《野人送朱樱》“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以“细写”对“匀圆”;《吹笛》“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以“律吕”对“关山”;《咏怀古迹》第二首“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以“怅望”对“萧条”(“萧条”是联绵字,但“怅望”不是联绵字);第三首“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以“朔漠”对“黄昏”(朔:觉韵字;漠:铎韵字,唐时两韵读音已经相近或相同。黄:匣母字;昏:晓母字,这是旁纽双声。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以双声的“清浅”对叠韵的“黄昏”,正是从老杜学来的。);第四首“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以“想象”对“虚无”(虚:鱼韵字;无:虞韵字,这是邻韵叠韵。)。这都不是偶然的。
《杜诗详注》(中华国学文库)
……
上面所说的语言形式的三种美——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总起来说就是声音的美,音乐性的美。由此可见,有声语言才能表现这种美,纸上的文字并不能表现这种美。文字对人类文化贡献很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始终是语言的代用品,我们要欣赏语言形式美,必须回到有声语言来欣赏它。不但诗歌如此,连散文也是如此。叶圣陶先生给我的信里说:“台从将为文论诗歌声音之美,我意宜兼及于文,不第言古文,尤须多及今文。今文若何为美,若何为不美,若何则适于口而顺于耳,若何则仅供目治,违于口耳,倘能举例而申明之,归纳为若干条,诚如流行语所称大有现实意义。盖今人为文,大多数说出算数,完篇以后,惮于讽诵一二遍,声音之美,初不存想,故无声调节奏之可言。试播之于电台,或诵之于会场,其别扭立见。台从恳切言之,语人以此非细事,声入心通,操觚者必须讲求,则功德无量矣。”叶先生的话说得对极了,可惜我担不起这个重任,希望有人从这一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完成这个“功德无量”的任务。
朱自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过去一般读者大概都会吟诵,他们吟诵诗文,从那吟诵的声调或吟诵的音乐得到趣味或快感,意义的关系很少……民间流行的小调以音乐为主,而不注重词句,欣赏也偏重在音乐上,跟吟诵诗文也正相同。感觉的享受似乎是直接的、本能的,即使是字面儿的影响所引起的感觉,也还多少有这种情形,至于小调和吟诵,更显然直接诉诸听觉,难怪容易唤起普遍的趣味和快感。至于意义的欣赏,得靠综合诸感觉的想象力,这个得有长期的修养才成。”(朱自清《论百读不厌》,见于他所著的《论雅俗共赏》第10页。)我看利用语言形式美来引起普遍的趣味和快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注重词句自然是不对的,但重视语言的音乐性,也是非常应该的。我们应该把内容和形式很好地统一起来,让读者既能欣赏诗文的内容,又能欣赏诗文的形式。
(本文节选自《语文讲话》第八章语言形式美,标题为编辑所拟)
《语文讲话》
王力 著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4775-9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汉语的特性
一、语音的特点
二、词汇的特点
三、语法的特点
第二节汉语的发展
一、语音的发展
二、词汇的发展
三、语法的发展
第三节汉语的亲属及其方言分类
一、官话方言,即华北方言、下江方言、西南方言
二、吴语
三、闽语
四、粤语
五、客家话
第二章 方言
第一节方言的语音
第二节方言的词汇
第三节方言的语法
第三章 语音
第一节汉语与四呼
第二节汉语与四声
第三节各地语音的异同
第四节古今语音的演变
第四章 语法
第一节词在句中的位置
第二节词是怎样构成的
第三节各地语法的异同
第四节古今语法的演变
第五章 词汇
第一节词汇与语音的关系
第二节词汇与意义的参差
一、同音词
二、同形词
三、同义词
第三节各地词汇的异同
第四节古今词汇的演变
第六章 文字
第一节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
第二节形声字的评价
第三节新字义的产生
第七章 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
第一节字形
一、正字和俗字
二、异体字
三、合流字
四、分化字
五、译名
六、别字
七、错字
八、意义各别
第二节字音
一、一字数音
二、误读的问题
第三节字义
一、北京的语汇
二、方言的语汇
第四节同义词、新名词、简称
一、同义词
二、新名词
三、简称
第五节古语的沿用
一、文言虚字
二、文言的语汇
三、过时的口语
四、复活的文言
第八章 语言形式美
第一节整齐的美
第二节抑扬的美
第三节回环的美
第四节诗的语言
第九章 语言与其他
第一节语言的真善美
一、语言的真
二、语言的善
三、语言的美
第二节语言的选择
一、什么话好听
二、把话说得准确些
三、语言的化装
四、观念与语言
第三节逻辑和语言
一、思维和语言的统一性
二、思维和语言的区别
三、概念和词
四、判断和句子
五、推理和复句
六、思维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
第四节语言与文学
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二、词汇与文学
三、语音与文学
四、语法与文学
第五节语言的规范化和通俗化
一、语言规范化
二、语言通俗化
原标题:《都说汉语美,到底美在哪?王力先生谈了这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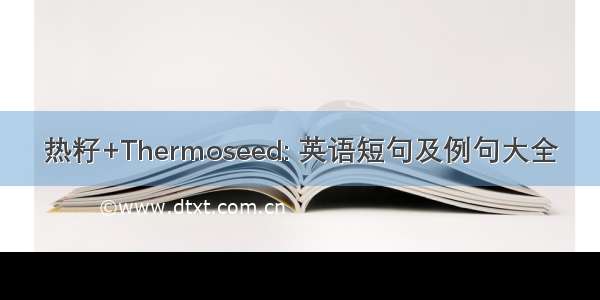
![[2024年]25句经典语录:启迪智慧的人生智慧](https://www.dtxt.com.cn/uploadfile/img/2024/05/24/b67359c4db45cf92ac939bc0043ba55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