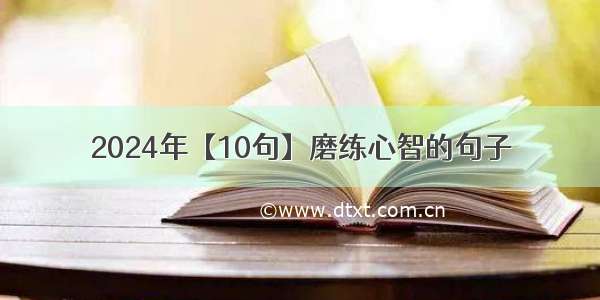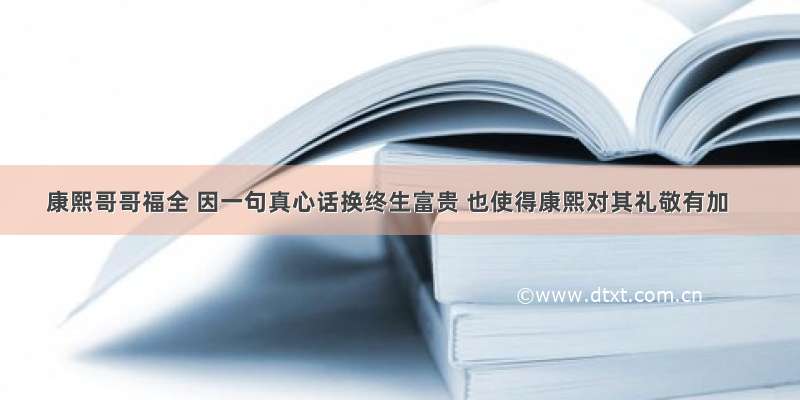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福全“身材魁梧,待人和蔼亲近。”他的王府在紫禁城以南,今台基厂二条中间路北。府中东北隅有花园,名“目耕园”。前人王逢《目耕轩》诗云:“身耕劳百骸,目耕劳两瞳”“目耕”二字,以农夫耕田比喻勤读不辍。福全为花园择此雅号,体现出其志趣所在。
一、一生淡薄,处事谨慎
福全一生淡泊宁静,“畏远权势”。他常在目耕园中款待文人、“礼接士大夫”,与学者名流切磋聚首,品酩畅谈。可以肯定,福全也曾多次在府邸接驾,恭迎玄烨光临。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巴林淑慧公主去世,玄烨率皇子及王公大臣送殡、“到裕亲王园,于公主枢旁恸哭”。巴林淑慧公主也是福全的亲姑,她死后停灵于福全府(很可能即在目耕园内),或许生前曾随侄儿同住府中?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八、九月间,玄烨巡幸塞外,福全随从前往。其间,与俄罗斯谈判边界问题的清廷使团,因途中受阻返归,与御营在塞外相遇。随团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写道:“位居一品的两位皇族亲王的与众不同的帐篷,就安扎在皇上帐篷的附近,其中一位是皇上的长兄”。“我们下马,荣幸地向两位亲王致意,他们对我们也以礼相待。被称为大王爷的皇上的长兄……和皇上的几个侍卫、统领长时间进行亲切的谈话。
他以及另外一位被称为赫都王(指肃亲王豪格之子)的亲王,穿戴都很朴素,他们的座骑看上去也很不起眼,只是配以一般的马饰,因此,你根本看不出两位亲王和别的清朝官员有什么区别。”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回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谈到玄烨的“两个亲兄弟”,说他俩对在清廷供职的西方传教士十分宽厚仁慈,并且“像其他方面一样,在这方面比其他所有亲王更显得突出。”可见福全与常宁,特别是福全,虽然身为皇兄(弟),但无丝毫傲气,平易近人,处事谨慎。这种作风很为玄烨欣赏。
二、与康熙帝的深厚感情
玄烨与皇兄感情深厚,孝庄在世时已是如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玄烨去盛京谒陵、这是他第二次东巡,期间,玄烨除去写信与祖母、嫡母报告行程,表达问候外,还单独给福全去信数封。
第一封写于三月初五日:“相别以来,忽复兼旬,棣萼之思,时在寤寐。初四日已抵盛京,山川形势,风土民情,深维祖宗开创之艰难,令人远想慨然。春气渐佳,知意兴甚适也。特此布问不宣。”十几天后,玄烨收到福全回奏,十七日又复一信:“顷览来奏,具悉念联之怀。兹者告祭事毕,巡行疆土,兼讲春蒐,正当草浅兽肥,弓燥手柔之时,且地多豺虎麋鹿,此乐惜不与王共之也。近状想佳,特此咨询”。
四月下旬玄烨踏上归途,路上再次寄谕福全:“别来未几,麦气迎秋,荏苒流光,良增思念,每阅来疏,足慰朕怀。兹东巡典礼,事事已毕,经过之处,无不喜见升平。二十日自盛京回銮,会面可期,布问不宣。”这几封书信没有凛然不可逾越的至尊口吻,比较亲切、自然。玄烨从千里之外频频慰渝,是对皇兄的特殊关怀。
三、心地善良但不善军事
心地纯厚的福全,绝非一名善于指挥,勇猛善战的骁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乌兰布通战役,是他一生中所参与的最重要事件,他与玄烨的关系,也从中经受了一次考验。
二十九年夏,噶尔丹以追索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名,进犯内蒙古乌朱穆沁地方,玄烨决定出兵歼剿。七月初二日,他任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胤禔做副手,率主力出古北口;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和多罗信郡王鄂扎做副手,出喜峰口;内大臣舅舅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等人,全部随军参赞军务。
这次出征由皇帝的亲兄弟挂帅,皇子佐之,指挥部成员除大臣外,还有几位宗室,表明玄烨对此役期望之高。
是年七月十四日,玄烨起程离京,名为巡视边塞,实际上准备亲临指挥。他很了解自己的兄弟,对俩人(特别是福全)的长处、短处与才力,无不清楚。认为只有亲自出马,从旁指导,才能必胜无疑。事实验证了他的顾虑。
玄烨踏上征途不久,突然患病,但仍勉力坚持,继续行进。到(七月)二十二日夜,他终因高烧不退,难以又撑,在大臣的一再劝请下,不得不由博洛和屯回銮、玄烨此病对这次战役,乃至清廷其后与准噶尔部斗争的事态发展,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八月初一日,清军在乌兰布通击败噶尔丹军。初三日,玄烨接到福全奏报,立刻命令他们“穷其根株”、“勿留遗孽“。可是,福全在得到这一指示前,为使将士得以休整,已经停止攻击,随后又听信前来为噶尔丹开脱的西藏喇嘛济隆等人的后,认为噶尔丹确有罢兵修好之意,竟向各路清军将领丁令暂停进击,因远地相隔,玄烨的阻止已无济于事,噶尔丹军在受到重创后,终于逃脱。这就是著名的乌兰布通之役、清军取得重要胜利、同时也留下很大余患。
平心而论,福全对清军此次出征未能全歼噶尔丹军,负有首要责任。事后,多罗信郡王鄂札等遵旨奏陈福全等人的过失,他们指出:“皇上深虑噶尔丹奸狡,此役不行剿除,必贻后患,多派精兵,尽发火器,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王大臣为参赞,指授方略,务期尽灭根株。乃福全等调度乖方,既经战胜,不能乘机剿灭,收兵又不鸣笳,贼败不行追杀,反行文禁止苏尔达等进兵,以致穷寇遁逃,殊误军机.且未经请旨,率兵擅回哈吗尔岭内。应将裕亲王福全、恭亲王常宁、简亲王雅布,俱革去王爵,福全撤去三佐领。……”因福全等错误严重,返京时“命止朝阳门外听勘”。举朝上下拭目以待,且看玄烨如何处理。
四、与亲侄子胤禔的矛盾,康熙明显偏袒兄弟
更使问题复杂化的,还有福全与胤禔之间的矛盾。这是玄烨第一次以亲兄、亲子互为搭档,他本希望俩入因是至亲,能更好地配合。不意恰恰相反,出征后叔侄对立,难以相处。八月十一日,玄烨谕大学士等:“胤禔听信小人谗间之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不相和协,妄生事端,私行陈奏,留驻军前,必致债事,著撤回京。”
如果叔侄间的矛盾不是异常尖锐.已影响前线指挥事宜,玄烨不会断然召回胤禔,因为这样做有损他本人的声誉。这也表明,从玄烨得知兄、子矛盾之始,就确定了以长幼尊卑为准绳的处理原则。
果然,当胤禔“以议政王大臣等取供时,应如何具供”向皇父请示时,玄烨回答:“裕亲王系汝伯父,议政王大臣等取供时,汝若与裕亲王稍有异同,朕必置汝于法,断不姑容。”被阻留在朝阳门外听勘的福全,“初亦录皇子胤禔军中过恶,欲于取供时告白。”
表明他本已作好被侄儿讼告,而受皇上责斥的准备。因为在他看来,父子、兄弟之情,毕竟难以相埒,何况他与玄烨又非一母所生。胤禔是玄烨的长子,一向为父器重,在他与胤禔的争执中,玄烨偏袒后者,乃人之常理。
加之他又贻误军机,遭到重斥事所必然然而,当福全与侄儿一起接受议政王大臣取供时,胤禔先说了一句:“我与伯父裕亲王供同”,此后便一言不发了。这使福全大为震惊。胤禔突然转变对立态度,显然是因玄烨事前已做嘱咐。面对玄烨的宽容与保全,福全百感交集,不能成言,更加惭愧与内疚。他“俯首良久,流涕曰,我复何言”,遂即一人全部承担了罪责。
未几,玄烨对福全等人的问题做出论定:“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为我军击败遁走,而领兵诸王大臣,不复追杀,反信济隆胡图克图议好之诈词,遣人语内大臣苏尔达等,令盛京、乌喇诸路兵,勿与之战。……如使苏尔达等邀击之,则噶尔丹可以就擒矣。伊等不战,乃大误也。福全等俱应依议治罪。但此举已击败厄鲁特兵,噶尔丹远遁,诸王大臣,概从宽免革,福全、常宁罢议政,与雅布俱罚俸三年,福全撤去三佐领。…”评价公允,处理宽大,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胸怀与用人策略。
福全等人的失误不仅产生严重后果,而且令玄烨深感难堪。乌兰布通之役,是玄烨继位后清廷第二次大规模出征。平定三藩之乱中,清廷调兵遣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前后共派出6名大将军,他们分别为亲王、郡王或贝勒。对此,玄烨曾明白解释:“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调遣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
与玄烨的期望恰相背驰,这些皇亲宗室在前线并不实心效力,而是彼此观望,拥兵自重,多次贻误战机。此次乌兰布通之役,玄烨特地让两个兄弟担任大将军,皇子佐之,个别亲王、宗室,只是作为并非主力清军的副统帅。这种安排表明,对于结束已近十年的平叛战争中宗室们的不佳表现,玄烨依旧耿耿于怀,因而想通过亲兄弟的成功事例,为之做出榜样,并借以教育宗室子弟。
但两位兄弟不争气,竟出此严重过失,使他在宗亲诸王大臣前大失颜面,内心自然十分恼火。更可虑的是,错此全歼良机,为清朝留下隐患,这成为玄烨的一大心病。尽管当时他从各种因素考虑,对上述忧虑未多流露,但数年后仍不得不承认:“前厄鲁特噶尔丹之役,官兵不能悉体朕意,即行剿灭,致失机会,罔奏肤功,朕心为之不怿。”“…六年以来,乌兰布通之役,时屬朕怀。”
乌兰布通之战成此结局,有一定偶然因素。如果玄烨不突然患病而是亲临指挥,必定穷追对手,不予姑息,噶尔丹军就可能全部被歼灭。如此,则无须数年后玄烨三次亲征,康熙朝中期的部分历史,也需要相应改写了。就福全来说,出现这一失误,不仅因他既无统兵作战的经验,又缺乏军事才能,还同他本人的性格、作风有一定关系。
乌兰布通战役后,玄烨再未重用福全和常宁,但清廷有重要政务,仍让他俩参与其中,给与效力机会,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玄烨主持多伦会盟,三十五年二月,玄烨第一次亲征噶尔丹,福全,常宁都在随从之列。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玄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率师离京。十一日,他写信谕告皇太子胤礽:“嗣后凡有谕令看阅之文,亦著裕(亲)王阅之。”胤礽立即照办,于当月十五日奏称,已将所录谕旨等,“奏报太后祖母,宫内遍令传阅。裕王、三阿哥(胤祉)及大臣等,俱已阅看。”三月二十五日,胤礽又在奏报中写道,已将皇父送回之折件,“送皇太后并宫内一览,裕王、大臣等一并看阅。”
由于玄烨的特殊关照,留在家中的福全得以及时了解大军征伐战况;在胤礽的奏疏内,福全被列于皇子、大臣之前、仅次于皇太后。这些情况都体现出玄烨对皇兄的看法,表明乌兰布通之役并没有在俩人之间留下裂痕。
五、福全最后的岁月,突显兄弟情深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玄烨第三次南巡,福全没有同往。五月玄烨返归,临近京城时,福全按约前去接驾,先期抵达等候的玄烨赋诗一首:
“候兄裕亲王”“花萼楼前别,已经春夏余。平明挂锦缆,日暮傍樵渔。吴越当年景,江湖各自知。留心民事重,隔己信音疏。”
当年秋,玄烨“命画工写御容与(福全)并坐桐阴,示同老意也。”不久,他又“咏桐老图赐裕亲王”“丹桂秋香飘碧虚,青桐迎露叶扶疏,愿将花萼楼前老,帝子王孙永结庐。”此时玄烨46岁,福全47岁,都已向老年迈进。
玄烨特在桐阴之下与兄并坐,让宫廷画师写真,是取兄弟二人同老同心,永远同在之意。
玄烨对福全的友爱、尊重和信任,还体现在下述事实上即福全与皇子们的不同亲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玄烨对后者的看法。
福全的皇侄众多。他去世前,十三阿哥胤祥之前的皇子都已在18岁以上,福全看着这些侄儿长大、熟知他们每个人的禀性、气质、能力与为人。皇子们在伯父面前,无须像在皇父前那样谨言慎行,毕恭毕敬,而他们的优点和短处,都得以充分表现。从某种角度说,福全对侄儿们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全面的。
由于种种原因,福全与侄儿们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诸皇子中,也最喜爱八阿哥胤禩。
一废太子期间,玄烨谈到胤禩时说:“..…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有的学者指出,福全去世前,曾向玄烨揭发皇太子胤礽的种种劣迹,同时赞扬胤禩聪明能干,品行端正,建议玄烨立后者为储君。这次谈话后不久,胤礽的主要支持者索额图即被拘禁,看来玄烨已考虑皇兄的建言,认为胤禩“是可以代替胤礽做皇太子的人选之一。”
福全能够向玄烨坦述对皇子们的看法,说明他虽然畏远权势,以宁静淡泊为本,但也绝非不关心政事,毫无政治头脑,而是有着自己的是非观点和爱憎。皇八子胤禩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福全去世时已23岁,一废太子前,他很受皇父器重,曾随扈参加第一次亲征,后又受封为贝勒,是享有封爵的皇子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还多次受皇父指派,与皇三子胤祉一起办理政务。不应否认。福全对于胤禩的赞赏,会促使玄烨对后者更加倚重;玄烨很重视长兄的意见,况且俩人对胤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受福全的影响、他的儿子们也与胤禩十分要好,彼此关系相当密切。
福全的早逝,使胤禩在储位之争中失去一位有力的支持者。如果福全健在,一废太子事件的势态发展与结果,以及胤禩本人的命运,或许都会有所不同。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十五日,福全的庶福晋纳喇氏生下他的第七个女儿,也是他最后一个孩子。
51岁的福全老来得女,又恰逢佳节良辰,可谓喜上加喜。然而,王府中的欢乐气氛没有持续多久,即因福全突然病倒而不复存在了。三月二十六日,玄烨亲至府中探望;五月六日、十四日,他从畅春园返宫间隙(当时孝惠住在畅春园,玄烨常往陪伴),又先后两次亲视福全疾。五月底,玄烨率领6位皇子巡视塞外,表明福全的病虽然不轻,但尚无大妨。
是年六月是一冷酷无情的月份,在不到二十天内,玄烨先后失去最后两位同辈至亲。六月初七日,常宁在京病逝。玄烨接到奏报、“命(在京)诸皇子经理其丧,并谕诸皇子每日齐集丧次,至发引后乃止。又给银一万两,命内务府郎中皂保监修坟莹立碑。”他绝未想到,更大的不幸会接踵而来。
当月二十六日,福全的病情突然恶化。二十七日深夜,玄烨在驻跸之地喀喇和屯得闻皇兄病笃,当即命全体随扈皇子星夜兼程,先赴京师,并不顾诸大臣劝阻,准备随即回銮。玄烨此刻还不知道,福全已于二十六日晚病逝。二十八日早晨,噩耗传至,怀着悲痛的心情,玄烨毅然踏上归途。由于正值盛夏(阳历七月),酷暑难当,一连数日他都是在夜间子时启行,赶赴京师。
七月初一日玄烨进入东直门,他没有回宮,而是直接赴福全府邸临丧。他摘除冠缨,“哭至枢前,奠毕,仍恸不已。”玄烨尚未抵达前,皇太后已先临王第举哀。对孝惠来说,福全虽非亲生,但作为母子,相处几达五十年,彼此也有一定感情。玄烨见到嫡母、只有相对唏嘘。他劝皇太后先行返宫,随即又命全体皇子及扈从诸臣,前往常宁殡所奠酒。他回宫后不入日常所居的乾清宫,而是来到景仁宫暂居。
当日,大臣们齐集景仁宫门前,奏请玄烨仍回乾清宫休息,以便继续去塞外避暑。玄烨没有同意,传谕说:“朕但想皇太后过哀,朕心不安耳。侯王殡后,朕再起程。至于居便殿者,非自朕始,乃太祖、太宗之旧典也。尔等不必恳奏。接着他又以“裕亲王之丧,皇子等理应穿孝,”令宗人府议奏。
宗人府认为只应让与裕亲王“同旗之皇子”穿孝,玄烨则不以为然:“裕亲王,朕之亲兄,岂可止令同旗皇子穿孝。”随命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穿孝”。除皇太子以外全体年长皇子为死者服孝,仅次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去世后的服孝规格,反映了玄烨对福全去世的哀悼程度。
六、康熙何以和福全关系至笃?
玄烨与福全感情笃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是康熙以汉族封建正统观念为标准对皇兄的愧疚。清朝入关前,并无严格的皇位继承制度。康熙十四年,玄烨学习汉族封建统治者立嫡立长的做法,将嫡子胤礽立为皇太子,表明他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是以汉族封建正统观念为标准。然而,他本人的继位,却恰恰偏离了这一准则。福临无嫡子,庶子中福全居长,继承皇位当为福全,而非排行第二的玄烨。
尽管这一结果是由各种因索造成,玄烨的继位完全名正言顺,但在玄烨的内心深处,始终对福全抱有歉意,这是由其很深的汉化程度与比较仁厚的禀性所决定的。虽然玄烨不可能承认这一点,但这却是贯穿在他与福全关系的全过程,并对之起有重要作用的一条隐线。
福全没有能成为福临的继承人,人们还有其它说法。一则说福全“向以损一目不得立”。一目失明,是个严重的生理缺陷,与健康的玄烨相较,福全自然处于劣势。一则是说福临临终前.“曾将他的长子召来,问他是否愿意执政?长子谦逊,自感年幼,不愿接受……于是顺治又把康熙叫来,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康熙较有教养,爽快地回答:他愿意遵照父命,承担社稷重任。这一回答博得了皇帝的欢心,遂即将皇位传给了他。”
根据福临染患天花后的病势等情况,后一说法难以成立,不过它却反映出福全、玄烨兄弟两人不同的个性气质:前者拘谨,胆子较小,后者果决而有魄力。这也正是他俩成年后各自伴随一生的性格特点,“由小看老”的古老民谚,是很有道理的。
福全性格特征的形成,与其自身的生理缺陷有一定内在联系。有残疾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感,何况同父异母弟玄烨自幼精力充沛,聪颖过人,这使福全从小就有自愧不如的潜在意识。
其次,玄烨完全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决定与家人的远近亲疏,严上下长幼尊卑之分。
福全不仅是他唯一的兄长而且是唯一比他年长(尽管仅大数月)的男性至亲。仅此一点足以使玄烨对福全的手足之情,比对常宁、隆禧更重。
第三,玄烨、福全的关系,还取决于福全本人。福全生性恬静,较少权欲之念,而且善于自保,是他始终保持与玄烨较好的兄弟关系,得以善终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既为其所处客观环境所迫,也与其从小形成的性格、气质很有关系。
他的存在,不仅没有对玄烨的集权构成任何威胁或不利因素,相反,却可以被玄烨用来作为宣扬封建伦常思想与手足和睦的一面旗帜,用以提高他本人在全体臣民,特别是汉族士大夫阶层中的声誉。这是福全身后,被玄烨树立为臣民榜样的本质所在。
从某种角度看,玄烨、福全这对君臣弟兄、好比两位相得益彰的和谐搭配。本应继位的兄长,对弟弟并无妒嫉,唯谨唯慎,处处谦让,恭顺有加;并非长子的继位者,对皇兄则极尽厚待与优宠。相互理解与体贴,不仅使双方从中获益,客观上还增加了对方的美德懿行,而两人的关系也自然越来越好,感情逐步加深。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